| 卡佛的小说,历来是“在表达着什么”,但也历来让你在“试图让自己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的。卡佛作文的收官之笔,每每形同在紧要时分掐断,读之愠怒,思之杳然。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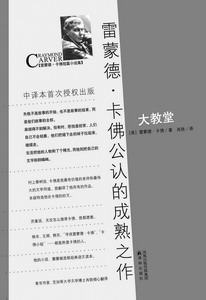 泰丽·夏沃(Terri.Schiavo)一案的一唱三叹,拜各处报章的连篇累牍所赐,我也算了解个七七八八。然而,论条分缕析、见微知著,丁林先生的《泰丽之死》(《万象》第七卷第八期)当属其中翘楚。美国朝野上下、寻常百姓,为了一个十五年前就被判定脑死亡的女人,为了讨论应该替她争取“生存权”还是“死亡权”,党派、司法、行政……制度舞台上的各种角色次第登场,国家机器的各个零件运转得井然有序却也让人怅然若失——你觉得谁都没有错,然而,又好像哪里不对劲。 泰丽·夏沃(Terri.Schiavo)一案的一唱三叹,拜各处报章的连篇累牍所赐,我也算了解个七七八八。然而,论条分缕析、见微知著,丁林先生的《泰丽之死》(《万象》第七卷第八期)当属其中翘楚。美国朝野上下、寻常百姓,为了一个十五年前就被判定脑死亡的女人,为了讨论应该替她争取“生存权”还是“死亡权”,党派、司法、行政……制度舞台上的各种角色次第登场,国家机器的各个零件运转得井然有序却也让人怅然若失——你觉得谁都没有错,然而,又好像哪里不对劲。
管子终究还是拔掉了。坚持了十三天才断气的泰丽,让人想起来还是如同凉风掠过刚拔掉牙的齿穴一般,酸酸地痛。人们无法摇醒沉睡中的泰丽,问问她,丈夫事隔多年——在另有女友和子女之后才“想起”代她主张的“有尊严地死去”,究竟是不是真话。再健全再滴水不漏的制度,也总有它们没有办法覆盖的盲区。人心是这盲区里最幽深最暧昧最无法用是非来衡量的角落,有时候探知那个角落的只能是同样幽深、暧昧、无法用是非来衡量的东西,比如,文学。
数年前我翻译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一组短篇,其中有一篇《不管谁在用这张床》(Whoever was using this bed)就曾在云山雾罩中,不露痕迹地将类似的问题悄悄推到世人的视线里,如今想起来简直像一道黑色预言。
故事照例是卡佛式的漫不经心,在极狭窄的空间内兜兜转转:一对曾经各自离异后重新组合在一起的中年夫妻,某夜突然被电话铃吵醒。丈夫去接,电话那头是个神神道道的女子,一开口就喊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执意要他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人来“聊聊”,最后丈夫只能挂断电话再把听筒挪开。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夫妻两个都来了精神,和衣坐起,又是抽烟又是喝咖啡,从电话说到梦再说到各自身上的病痛,不知怎么扯到了死。妻子说到一则新闻:“你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那家伙拎着一把猎枪跑进一间重症监护病房,逼着护士把他父亲的生命维持仪器的插头拔掉?”于是,夫妻俩就在这夜半时分,开始讨论有朝一日万一此等大难临头,那根管子究竟应该“拔,还是不拔”。讨论越来越偏离闲聊的轨道,妻要夫发誓“替我把插头拔掉,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夫要妻允诺“别帮我拔掉,让我活下去,行吗?”谈话到了这一步,两个人自然都再没有了入睡的可能,于是起床、吃早饭、上班。然而,整个白天,丈夫都神思恍惚,“仿佛看到一张病床……床上支着一张氧气幕。床边是那些屏幕,大监视器什么的——就是电影里的那种玩意”。回到家,丈夫语无伦次地说,“好吧,如果你想听我就告诉你,我会替你把插头拔掉的,如果你想让我这么干,那我就会去做……不过,我说过的关于‘我的插头’的话还是算数的……我已经把每一个角落都考虑遍了。我已经精疲力尽。”
两个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女人,这回她的口气平静而有条理,但还是固执地寻找她的男人。丈夫开始发火,威胁“我要把你的脖子拧断”,一旁的妻子飞快地附身把电话掐断。丈夫觉得自己的声音“在表达着什么,可是,正当他试图让自己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时,便什么都听不见了”。小说就此打住。
卡佛的小说,历来是“在表达着什么”,但也历来让你在“试图让自己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的。卡佛作文的收官之笔,每每形同在紧要时分掐断,读之愠怒,思之杳然。这一篇,正确而空泛的理解不过四个字——中年危机。激情渐退、惶惑终日,凡此种种,都可以往这顶帽子里套。然而,总有一些细节是游离于表层之外的,比如:这一对夫妇以前大约都经历过跌宕情事,丈夫的前妻和孩子至今也常来电话骚扰,因此,他们养成了每晚入睡前拔电话的习惯,偏偏那一晚,他们忘记了拔(拔电话的现实和拔“插头”的臆想互为镜像,形成饶有趣味的对照),斜刺里就杀出一个不速之客;这场婚姻本身也处在微妙的瓶颈阶段,妻子曾经在梦里呼唤别人的名字,以至于那天晚上,丈夫就这样问被惊醒的妻子:“这又是一个没有我的梦吗?”
如此想来,卡佛真正欲言又止的,还是孤独吧——人终究是要从孤独里来,往孤独中去。为了摆脱孤独,人们离婚了以后又结婚,寻找丢失的爱人、半夜里起来赌咒发誓。然而,没办法,我们还是看到那张“支着氧气幕”的病床在眼前越来越清晰;我们知道,当我们躺在里面的时候,没有人能代替我们面对未知的孤独,等待奇迹,或者,终结。
小说里那对夫妻不停地要求对方答应自己的“遗嘱”,那种偏执与絮叨让你不能不相信:婚姻比生命更脆弱,而比婚姻更脆弱的,是信任。鼻尖沁着汗珠子站在饭店里浇香槟塔的新婚夫妻们,大约怎样的海誓山盟都经不起心上偶然掠过的一丝疑问:当你成了一株准植物、静静躺了十五年之后,你的他(她),会替你做怎样的决定?
卡佛数十年前的虚拟设问,在公元2005年的真实生活里,得到了答案——当然,只是众多可能的答案中的一种,却也是经过了各个层面的平衡、在现有条件下最政治正确的一种。泰丽一家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好人,他们遭遇的是经典意义上的悲剧。维系泰丽生命的那根管子,在政治家医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宗教人士媒体从业者看来,或许是口号是机遇是新课题是收视率是改写历史的分水岭;然而,在数千万不那么专业的民众看来,它或许更接近于卡佛藏在小说里的一声叹息,一道清晰标记着人类终极命运的指路牌:前方,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