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books&idArticle=74650
过年回家,点检旧帙.陶诗”蔼蔼堂前林,贮我以清阴”,而我贪恋的,无非横斜乱书所贮的时光和气息罢了.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的结尾谈起了他重读托马斯曼<魔山>的体验:多年前在肺病疗养院初读<魔山>的光阴,多年后重读<魔山>的光阴,还有,<魔山>本身作为艺术品想象中的光阴,交融难辨.我自觉很能契会这况味的:宛如拉图尔画笔下的阴影和烛光.这时候,我很少真正想读什么.但这次,信手抽出的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不知多少年没碰过这本书了,竟有点儿”十年旧约江南梦,重听寒山半夜钟”的惘然.不消说,又忍不住重读了遍书中那篇<夜行的驿车>.一文读竞,从惘然里滋生的,却是疑惑.
遥想年少,对<金蔷薇>的解读不可避免的源自刘小枫那篇<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吧. <夜行的驿车>多年来留在心头的印象也正是那句”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金蔷薇>,对我来说则是个符号,背后指向着刘小枫为我们刻画的”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以羞涩和虔敬为素质的怕”,以及”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在这里,几乎任何一点对柔顺和隐忍的不理解都是莫大的原罪.
很难说<金蔷薇>的文字本身能无可争议的印证这种阐释吧.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无言地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满含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
多年来,这些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俄罗斯文学,艺术,思想的认知.<战争与和平>里的”小人物”图申和卡拉塔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的哲学著作,塔可夫斯基的<安德列鲁勃廖夫>…..岁月流逝,今日不经意的一次重嗅蔷薇,心头唤醒的倒是怀疑之虎.我以为,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式的解读片面化了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精神.甚至,也片面化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刘小枫说:”…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醒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乘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素质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而在我今天看来,太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苦难虔敬的同时,身上似乎又都不可救药地带着童稚般的诗意而固执的狂想,这分狂想恰恰拒绝意识自身的渺小和欠缺.爱丁堡说,诗人巴尔蒙特一生只写了一句好诗:”我来到世间/是为了看一看太阳”.斯克里亚宾认为自己的天职是创作一首从未有过的曲子,当全世界钢琴家同时弹奏它时,弥赛亚便会降临.费奥多罗夫在<共同事业的哲学>里告诉我们,人类的使命是让祖先复活,”祖先遗骸的微粒遍布物质…..不管一个微粒如何碎裂,裂开后都会保留断口的痕迹,这些微粒最终可以对接起来,还原成昔日的人体”.托尔斯泰,就连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蒲宁都指出过他身上的异教徒精神,以及,狂妄自大:”环绕自己八万俄里”------ 我承认,我很天真幼稚,写到这里,总归忍不住(虽然写跑了题)抄一下托尔斯泰讲的”蚂蚁兄弟”故事:”我五岁,三哥六岁,二哥七岁.十一岁的大哥向我们三个弟弟宣布他有一个秘密,这秘密一旦被揭示…谁也不再生谁的气,人人彼此相爱,成为”蚂蚁兄弟”…..我们甚至想出一种蚂蚁兄弟游戏,也就是找几把椅子,用些箱子盒子把它们围起来…然后我们几个钻到椅子下面去紧偎在一起坐在黑暗中.我记得我体验到了爱和动情的特殊感情…..蚂蚁兄弟是什么….大哥说他已经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要想能听到这个秘密,除非沿着地板的缝隙走一遍的时候心里一点也没想到一只白熊),而这根小绿棒又埋在了老禁伐林那个山沟旁的大路边.为了纪念大哥,我请求把我葬在那里…..”-----我时常觉得,夏伽尔也许比列宾和列维坦更深刻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
<金蔷薇>的另一种译本名为<金玫瑰>,译者是戴骢先生.写到这里,我却没去再把这个译本找出,不知怎么,这一刻,”金玫瑰”这几个字(以及那篇我熟读过的<珍贵的尘土>)让我想起了马拉美,想起了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甚至想起了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而窗外,春阳是舒缓的,早寒也淡远虚无,不可捉摸,仿佛舒缓中的些微感慨.我宁愿想起<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结尾,我宁愿想象普里什文笔下的夏天,大地辽阔,森林明朗.我宁愿在这些想象中抄写<金蔷薇>结尾一篇<对自己的临别赠言>中的一句:”应该沉浸在风景中,好象把脸埋在一堆给雨淋湿的树叶中,感觉到它们的无限的清凉,它们的芬芳,它们的气息一样”…….
“金蔷薇”的迷信
2006-08-23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廖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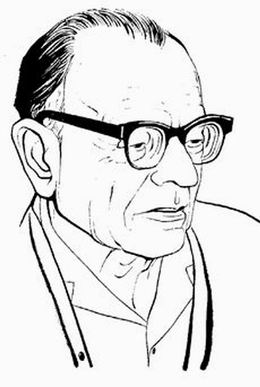 |
|
帕乌斯托夫斯基 |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之后,在20世纪,除了拿到诺贝尔奖的几位俄罗斯顶尖作家的小说之外,对于俄罗斯小说的评价和研究程度似乎比诗歌要低得多,布尔加科夫、爱伦堡以及这两年突然走俏的巴别尔等四五人就算是少有的例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在几位学者的动情鼓吹下,一时间《金蔷薇》确立的那种抒情传统,似乎成了上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但我个人认为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个很缺少思想能力的平庸作家,作品充满了让人昏昏欲睡的感染力。
我一直试图在这种传统中发掘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可惜迟迟没有收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抒情散文,这其中同样有浓重的人世之哀,思乡之愁,但同样是忆旧,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康斯坦丁・费定的文章就乏味而冗长。他是个严重缺少整体感,也不善于捕捉细节的作家,他的每一段叙事都缺少一个扎实有力的句号,他拿起一个话题说事儿――比如说费定爱语言,比如说他爱大自然――说着说着就莫名其妙走失,不知自己说到哪儿了,等你回过神来,他的“故事”好像已经讲完了,只见费定还在那儿爱他的语言和大自然,爱啊爱啊爱个没完。
这特点给人一种不大好的感觉,即:许多俄罗斯的散文随笔都在风格上过于相似,不同人写出来的东西却都大同小异。七八年前学林出版社的一套“白银时代俄国文丛”,样式美观且价廉,然而一读之下,却发现这些人不管是待在国内的还是流亡国外的,都比较忠于同一种写法。把沃洛申的日记和吉皮乌斯的回忆文字穿插放在一起,看不出太多区别来:都是潦潦草草的随手记,短句多,偏重印象式的叙述,缺少细节刻画,我怀疑有多少人有耐心拿它们当文学作品来品读。
以我个人浅见,这也许是90年代末,“白银时代”虽然很热了一阵,但始终没有出现让人能够至今回味良久的文选、文集的原因之一。那一代以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为旗帜的文人,他们的灿烂成就不容否认,但就以现有的中译作品来看,似乎都欠缺19世纪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沉郁、厚实的思想能力,而另一面,其对民族性、对一种传统近乎习惯性的执守也许对翻译和异域读者的接受造成了足够的障碍。而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白银时代之后的散文,也只有帕乌斯托夫斯基那一路“纯粹”而“耽美”的了,而所谓“耽美”的另一面,就是一脉相承自白银时代的零散、琐碎、芜杂。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既凝聚了生命的沉痛又拥有精致形式的回忆性散文,实属难得一见。
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五年散文精选集《布拉格一瞥》中收录了几篇俄苏散文,其中有两篇流亡女作家苔菲的文字。这位笔名苔菲的女子,著名文学史家阿格诺索夫说她擅写幽默、乐观的小品,但就这两篇文字而言,她的幽默感并不明显,而那种缺少整体感、不讲究细节的散漫写法仍是很眼熟的,比如喜欢下一些励志式的结论,喜欢随意加入“啊”、“哦”之类语气词,写博客倒是比较合适。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方面的理解和审美值得反省一下,或至少反省一下在引介中有无偏差。那么多白银时代诗歌、散文、随笔、回忆录,可我们现在谈到俄国人的回忆录仍只能想起19世纪的赫尔岑、20世纪的爱伦堡的两部大书,以及早在十多年前就引进的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谈到俄国诗歌,外国文学出版社在90年代初的一套开本很小、印量极少的“小白桦译丛”,其文字的优美度绝对超过“白银时代”热时期各种厚厚的诗选,以及近几年间的一些新译的诗人文集。这不仅关系到译者的技术高低,同样也关系到我们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认识是否全面,我们的选择范围是否过于狭小。举个最近的例子:我实在没看出来普里什文这样的“大自然作家”有什么必要出堂皇的五卷本,大自然美则美矣,但帕乌斯托夫斯基那一路东西,真还有那么多人爱看么?